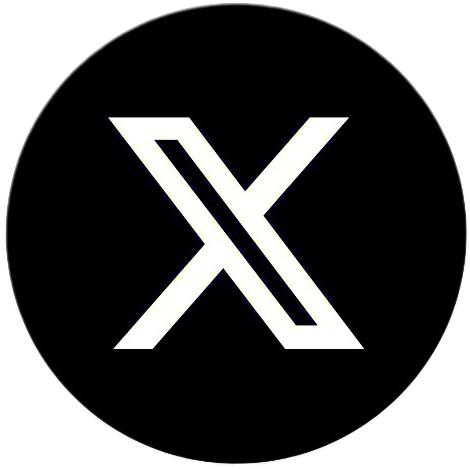肝脏巨噬细胞来源和功能复杂, 包括肝脏固有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来源的浸润巨噬细胞, 在宿主防御机制及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也是参与肝脏损伤和修复的主要细胞成分. 解析不同来源肝脏巨噬细胞在不同病因导致肝损伤过程中表型分化、生物学作用的动态变化及其分子机制, 对理解肝损伤的病理过程, 探索以肝脏巨噬细胞为靶点预防和治疗肝损伤以及肝纤维化的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固有巨噬细胞; 浸润巨噬细胞; 肝损伤
核心提要: 肝脏巨噬细胞来源和功能复杂, 解析不同来源肝脏巨噬细胞在肝损伤过程中表型分化、生物学功能的动态变化及其分子机制, 对理解肝损伤的病理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引文著录: 李静, 季菊玲. 肝脏巨噬细胞及其在肝损伤中的作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7; 25(14): 1223-1230
Liver macrophages: Role in liver injury
Jing Li, Ju-Ling Ji
Jing Li, Ju-Ling Ji,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Medical School of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01, Jiangsu Province, China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572871 and No. 81761128018;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No. BK20151277.
Correspondence to: Ju-Ling J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Medical School of Nantong University, 19 Qixiu Road, Chongchuan District, Nantong 226001, Jiangsu Province, China. jijuling@ntu.edu.cn
Received: March 7, 2017
Revised: March 20, 2017
Accepted: April 5, 2017
Published online: May 18, 2017
0 引言
肝脏巨噬细胞由固有和浸润巨噬细胞共同组成, 表型和功能复杂, 在维持肝脏正常生理功能以及各种毒物、药物和病原微生物引起的肝脏损伤以及各种肝脏代谢性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始终是肝脏病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 近年来免疫微环境在各种肝脏病理状态下所起作用日益受到关注, 作为肝脏局部免疫的重要组成, 肝脏巨噬细胞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类研究的焦点[2]. 本文将结合这一领域近年的研究进展, 对巨噬细胞、肝脏巨噬细胞的来源、分化及其在肝脏损伤中的作用作简要回顾.
1 巨噬细胞
一百多年前, 俄国生物学家élie Metchnikoff观察到血液中的某些白细胞可在炎症局部聚集, 推测这些细胞具有攻击并杀灭病原体的作用, 建议将其命名为巨噬细胞, 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细胞免疫学说[3]. 为此Metchnikoff与提出体液免疫学说的德国科学家Paul Ehrlich分享了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巨噬细胞在体内分布广泛, 是天然免疫系统的关键细胞成分, 主要通过受体介导的吞噬作用, 或释放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氧代谢产物或蛋白酶等, 识别清除坏死或凋亡细胞碎片, 细菌和寄生虫等病原体, 也能直接杀伤肿瘤细胞. 作为专职抗原递呈细胞, 他们也处理并通过MHC-Ⅰ(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Ⅰ)和MHC-Ⅱ(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Ⅱ)类分子递呈抗原, 参与适应性免疫[4]. 在病原体感染或组织损伤时, 激活的巨噬细胞释放多种细胞因子, 如: 白介素(interleukin, IL)-1和TNF-α等, 参与和促进炎症反应; 同时分泌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α和β(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 1-α and β), 也称为CC亚族趋化因子3和4(C-C motif chemokine 3, CCL3; C-C motif chemokine 4, CCL4), 以及IL-8等趋化性细胞因子募集其他免疫细胞到局部参与发挥抗感染或组织修复作用[5].
1.1 巨噬细胞的来源
巨噬细胞可以分为浸润和固有巨噬细胞两大类[6]. 未成熟的单核细胞从骨髓释放, 进入血液循环, 在血液中存留数小时至数日, 即移行至全身各组织器官内, 分化为单核细胞来源的浸润巨噬细胞. 固有巨噬细胞广泛分布于全身各组织器官, 根据分布组织不同其命名各异, 如: 在脑部为小胶质细胞, 在皮肤为Langerhans细胞, 在肝脏为Kupffer细胞[6-8]. 有关固有巨噬细胞来源的讨论持续不断. 传统观点认为, 在发育的胚胎期和围生期, 从血中募集的造血前体细胞在组织局部分化为固有巨噬细胞[8,9].
直到1999年, Alliot等[10]在第8天小鼠胚胎的脑原基中观察到小胶质细胞, 并确认其起源于卵黄囊, 在整个胚胎期持续活跃增殖, 直到出生后2 wk, 人们开始认识到胚胎发育过程中单核巨噬细胞可来源于卵黄囊原始巨噬细胞[11]. 整个成年期, 小胶质细胞依靠自身较长的存活时间和自我更新保持稳定, 不依赖造血细胞的补充. 10年后, 以上发现在采用Cx3cr1gfp/+转基因小鼠进行的单核巨噬细胞谱系追踪的研究中得到证实[12]. 2012年, 同一研究小组通过谱系追踪确认皮肤中的Langerhans细胞主要来自胎肝中的造血组织, 成年期也具有自我更新保持稳定的能力[13]. 与此一致的是在散发或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单核细胞减少症患者, 皮肤中的Langerhans细胞成分不受影响[14] .
2013年Yona等[15]通过构建单核巨噬细胞特异性CX3CR1启动子介导Cre重组酶表达的转基因小鼠, 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单核及巨噬细胞fate-mapping研究, 证实包括肝脏、肺泡、脾脏和腹膜腔等的多种组织中的固有巨噬细胞在出生前就已经形成, 并在成年期通过自身增殖维持种群. 同期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胚胎早期在多种组织中可检出卵黄囊衍生而来的CD45+CX3CR1hiF4/80hi巨噬细胞, 其发育受转录因子PU.1调控. 而造血干细胞来源CD45+CX3CR1+F4/80lowCD11bhi巨噬细胞的发育依赖于转录因子Myb. 卵黄囊衍生的巨噬细胞在Myb敲除小鼠中能正常发育, 但在PU.1敲除小鼠中不能正常发育. 实验将CD45.1小鼠的正常骨髓细胞经静脉注入条件性敲除Myb以去除造血干细胞的CD45.2小鼠体内形成骨髓移植嵌合体, 3 mo后发现嵌合体中所有外周单核细胞和组织F4/80lowCD11bhi巨噬细胞均来自供体CD45.1小鼠; 而肝、脑和皮肤中的F4/80hi巨噬细胞均来源于受体CD45.2小鼠[16]. 我们课题组在最近通过照射破坏骨髓构建的CD45.1/CD45.2小鼠骨髓移植模型中也得到了一致的结果(未发表数据). 2016年, Scott等[17]在白喉毒素清除肝脏固有巨噬细胞的小鼠模型中证实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能迁入血窦转变为寿命长且能自我更新的固有巨噬细胞. 据此推测, 组织中的固有巨噬细胞可能主要由两个亚群组成: 一群是来源于卵黄囊的F4/80hi巨噬细胞, 在状态稳定的成年动物中持续存在, 不依赖于造血干细胞; 另一群来源于骨髓的F4/80low CD11bhi巨噬细胞, 可以通过骨髓前体细胞替代更新.
1.2 巨噬细胞的极化
巨噬细胞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细胞群体, 主要表现为其所产生的细胞因子、表面标志物以及基因表达谱具有显著的多样性. 1992年, Stein等[18]报道由IL-4诱导分化的巨噬细胞与传统的干扰素γ(interferon-γ, IFN-γ)诱导激活的巨噬细胞在表型和功能上均有差别, 因此IFN-γ诱导的巨噬细胞激活途径被称为经典途径, 经此途径激活的巨噬细胞称为经典激活型巨噬细胞; IL-4诱导的巨噬细胞激活称为替代途径, 相应的巨噬细胞称为替代激活型巨噬细胞. 数年后, Mills等[19]将巨噬细胞的激活分化与Th1和Th2型免疫反应关联起来, 提出了M1-M2的名词. 经典激活型巨噬细胞(M1)和替代激活型巨噬细胞(M2)巨噬细胞不仅在功能和基因表达谱上有显著的差异, 他们的代谢作用也不同, M1型糖酵解增强, 分解精氨酸产生一氧化氮增加; M2型依赖脂肪酸氧化, 通过精氨酸酶分解代谢精氨酸[20].
Th1细胞因子(如: IFN-γ)诱导产生经典激活型巨噬细胞, 又称为M1[19,21]. Th1淋巴细胞主要参与针对细胞内细菌和原虫感染的免疫反应, 由IL-12和IL-2激活, 产生的细胞因子主要是IFN-γ. IFN-γ能激活巨噬细胞吞噬并降解胞内感染的细菌和原虫, 并激活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 分解精氨酸生成NO, 直接杀灭细菌和原虫. 除IFN-γ外, 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 LPS), 以及一些细胞因子, 如: TNF-α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也能诱导经典的M1型巨噬细胞活化. M1型巨噬细胞具有产生大量促炎因子(如: IFN-β, IL-12, TNF, IL-6, and IL-1β) , 趋化因子(如: CCL2, CXCL10, CXCL11), 以及反应性氮和氧自由基; 高表达MHC抗原递呈分子、共刺激分子等, 促进Th1免疫反应的作用; 是杀灭病原微生物、抗感染的重要效应细胞[22]. M1的激活途径受到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STAT1(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STAT1)[23], 核因子-κB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等多重信号通路调控[24].
Th2细胞因子(如: IL-4, IL-13)诱导产生的替代激活型巨噬细胞又被称为M2型巨噬细胞[19,21]. Th2淋巴细胞主要参与防御胞外寄生虫(包括肠道蠕虫)感染的免疫反应, 由IL-4激活, 并产生IL-4, IL-10, 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IL-5, IL-13等细胞因子. 此外免疫球蛋白IgG, IL-10和糖皮质激素等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通路诱导M2型分化, 促进Th2免疫反应. 目前, 根据诱导方式的不同, M2又可分为三种不同亚型, 包括IL-4和IL-13活化的M2a型巨噬细胞; 由免疫球蛋白Fc受体和免疫复合物活化的M2b型巨噬细胞; 由IL-10、TGF-β、GCs活化的M2c型巨噬细胞[25]. M2型巨噬细胞甘露糖受体、C型植物血凝素1和精氨酸酶表达增加, 具有抗寄生虫感染、促进细胞生长, 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 细胞产生IL-10, TGF-β和前列腺素E2等细胞因子增加, 而MHCⅡ类分子表达减低. M2型巨噬细胞在促进组织修复和抑制炎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6]. M2的激活途径受到STAT6和锌指转录因子等信号通路调控[27].
Th1/Th2模式对于T细胞异质性和巨噬细胞极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依据激活途径不同将巨噬细胞划分为M1型或M2型便于表述巨噬细胞的功能和表型, 因此一直被沿用至今. 但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并不能充分体现巨噬细胞亚群复杂的生物学特性[28]. M1/M2分类仅考虑了体外特定细胞因子或配体对巨噬细胞表型的影响, 以及体内特定病变中与Th1/Th2型细胞反应相对应的巨噬细胞亚型; 但忽略了刺激的来源和发生的背景, 忽略了M1/M2型激活信号在组织中并非独立存在的事实, 忽略了激活的巨噬细胞可能并不形成清晰的M1或M2亚型, 其扩增也并非克隆性的. 多数病理状态下, 很难明确组织巨噬细胞是经典激活型还是替代激活型, 单个巨噬细胞可同时表达M1型和M2型表面标记, 因此有必要建立更全面的巨噬细胞分类系统.
2 肝脏巨噬细胞
生理状态下, 肝脏巨噬细胞主要是固有巨噬细胞, 即枯否细胞, 发生损伤的肝脏中巨噬细胞则由外周血单核细胞来源的浸润巨噬细胞和肝脏固有巨噬细胞两部分组成. 如前所述, 学者们曾普遍认为来源于骨髓的外周血单核细胞到达肝血窦后分化为固有巨噬细胞, 且骨髓来源的单核细胞参与固有巨噬细胞的更新[29]. 因此早期的相关研究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 缺少对浸润和固有巨噬细胞的区分. 近年来研究表明肝脏损伤早期固有巨噬细胞数量减少, 之后通过自身增殖补充, 这种增殖与趋化到局部的外周血单核来源巨噬细胞无关. 2014年, Zigmond等[30]在急性肝损伤模型中, 再次证实浸润的外周血单核细胞不参与损伤过程中肝脏固有巨噬细胞的补充, 后者可自我更新; 来源于外周单核细胞的浸润巨噬细胞与固有巨噬细胞的基因表达显著差异, 提示两者是具有不同起源和不同生物学功能的细胞群体.
肝脏固有巨噬细胞位于肝血窦内, 胞体呈星形, 细胞核大而圆, 胞质丰富, 内含大量核糖体和吞噬体, 其胞浆凸起可附着于内皮细胞表面, 伸入内皮细胞间隙或窗孔至血窦外, 表达F4/80、CD11b和CD68等巨噬细胞表面标志. 肝脏固有巨噬细胞占肝内细胞总数的15%, 固有巨噬细胞总数的80%-90%, 构成全身最大的固有巨噬细胞群[1]. 生理条件下, 由于接受门静脉和肝动脉的双重血供, 肝脏持续暴露于经胃肠道静脉系统吸收的高浓度食物抗原和来源于肠道共生菌群的细菌组分. 因此肝脏需要高度协调的天然免疫机制来避免这些无害物质激发的炎症反应. 肝脏固有巨噬细胞则是维持肝脏耐受状态的重要细胞成分, 其表面分布有高密度的清道夫受体和模式识别受体, 包括: 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 TLR)和Nod样受体, 能检测到病原体相关模式分子和危险信号分子. 肠道细菌产物LPS能通过TLR4激活肝脏固有巨噬细胞, 产生包括: TNF-α, IL-1β, IL-6, IL-12和IL-18等多种促炎因子和趋化因子[31], 不仅能非特异地吞噬和清除血流中的细菌、异物等抗原性物质, 平衡持续不断的免疫原刺激, 抑制T细胞激活, 促进免疫耐受; 而且还具有特异性免疫应答、抗肿瘤免疫、内毒素解毒、抗感染、调节微循环及物质代谢等方面的作用[1,2].
药物毒物、代谢、病毒等各种原因导致的肝损伤中, 固有巨噬细胞激活, 分泌多种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引起无菌性炎症和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等炎症细胞浸润, 进一步加重肝损伤[32-34]. 单核细胞的浸润主要受趋化因子CCL2, 又称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及其受体趋化因子受体CC族受体2(Chemokine receptor, CCR2)的调控[35,36]. 单核细胞来源的浸润巨噬细胞在急性和慢性肝损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并参与肝脏病变的消退. 尽管肝脏固有和浸润巨噬细胞有很多相似性, 仍然可以通过一些表面标志加以区分. 如F4/80和CD11b可用于小鼠肝脏固有与浸润巨噬细胞的鉴别, 肝脏固有巨噬细胞表型为F4/80hiCD11blo, 而浸润巨噬细胞表型为F4/80lo CD11bhi[37].
根据其从局部微环境中接受的信号, 激活的肝脏巨噬细胞可以表达M1或M2型巨噬细胞的分子标志物. M1促炎型和M2抗炎型固有巨噬细胞的动态平衡调控着肝脏内的炎症反应[38]. 但M1和M2的概念对于肝脏巨噬细胞或许过于简单. 对各种损伤刺激作用下肝脏浸润巨噬细胞的转录组学研究[39]提示活化巨噬细胞的基因表达谱分布在M1到M2这两极之间. 某些巨噬细胞不能被简单归于M1或M2. 部分骨髓来源的浸润巨噬细胞转变为与组织重塑有关Ly6clo亚群, 出现M1和M2之外的表型, 包括: 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eptidase 9, MMP-9), MMP12,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以及非转移性黑色素瘤糖蛋白B等表达增加[40]. 损伤肝脏中的浸润巨噬细胞甚至有可能来自腹膜腔, 这些F4/80hiGATA6+巨噬细胞依赖CD44和ATP穿过间皮进入肝实质, 迅速增殖转化为M2型[41].
3 肝脏巨噬细胞与肝损伤
机体的固有免疫系统既可通过识别保守的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对病原微生物的感染作出应答, 也可通过识别组织损伤过程中释放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DAMP) , 引发非感染性炎症[42]. 坏死肝细胞释放的高迁移率族蛋白1和热休克蛋白70等DAMP分子可激活包括肝脏固有巨噬细胞在内的免疫细胞, 引起非感染性炎症. 最近的多项研究[43,44]发现损伤肝细胞释放的胞外囊泡中携带有特定miRNA以及TRAIL, CXCL10等细胞因子, 也具有激活或趋化巨噬细胞的作用.
3.1 药物和毒物性肝损伤
对乙酰氨基酚(acetaminophen, APAP), 即扑热息痛, 是目前应用最广的解热镇痛药, 也是引起急性肝损伤的重要原因[45]. 高剂量的对乙酰氨基酚可使细胞色素P450 2E1活性增强, 产生大量毒性物质 (NAPQI、亲电子基、氧自由基), 引起肝细胞严重损伤, 释放DAMP[42]. 在欧美国家, 每年约有45%的急性肝衰竭患者由过量使用APAP引起. 动物肝损伤模型常用的CCL4对肝脏的损伤机制与APAP类似, 其代谢产物三氯甲基自由基(CCL3)等具有极强的氧化能力, 可导致细胞质膜或亚细胞结构的膜脂质过氧化, 肝实质细胞损伤. 药物毒物导致的肝损伤急性期, 肝脏固有巨噬细胞数量显著减少, 恢复期通过自身的增殖补充, 不依赖于Ly6chi循环单核细胞. 坏死炎症期, Ly6chi循环单核细胞通过依赖CCR2和M-CSF介导的信号通路被募集, 大量涌入肝脏, 导致肝脏巨噬细胞总数急剧增加[35]. 这些Ly6chi浸润巨噬细胞在消散期转化为Ly6clo巨噬细胞. 阻断这些细胞的浸润, 会影响损伤修复[46]. 基因表达谱显示, 稳定状态和损伤恢复期的固有巨噬细胞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而恢复期固有和浸润巨噬细胞的表达谱完全不同[30]. 恢复期, 浸润巨噬细胞表达促血管生成、抑制中性粒细胞激活浸润、促进中性粒细胞清除的多种介质和因子, 获得了促进组织修复的表型[30,46].
3.2 酒精和非酒精性肝损伤
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和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是慢性肝损伤的重要原因, 最终发展为酒精性肝炎或非酒精性脂性肝炎、肝纤维化、硬化[47]. 两者均以肝细胞内游离脂肪酸的聚集, 脂变为主要病理改变. 美国48%肝硬化相关的死亡与ALD有关, 我国ALD发生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ALD是肝脏损伤的原因较为复杂. 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不仅通过细胞毒性和氧化应激直接损伤肝细胞释放DAMP, 还增加了肠道对于肠道菌群产生的内毒素-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 一种细菌性的PAMP)通透性, LPS随血流进入肝脏, 结合并激活肝脏巨噬细胞[33,48]. NAFLD是西方国家最常见的慢性肝病, 在全世界范围的发病率也逐年增加. "肠-肝轴"学说在NAFLD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 NAFLD患者肠道菌群失调、通透性增加, 导致通过门脉系统进入肝脏的LPS增加, 激活的肝脏固有巨噬细胞[49]. 而肝脏固有巨噬细胞表达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可能具有抑制NAFLD炎症反应和纤维化的作用[50].
ALD和NAFLD中激活的固有巨噬细胞产生IL-1β, TNF和IL-6等促炎因子加重肝脏的损伤, 并趋化单核细胞进入肝脏转化为浸润巨噬细胞, 浸润巨噬细胞在ALD和NAFLD肝脏炎症损伤和组织修复中均发挥着关键作用[37]. 同样根据Ly6c表达水平, 浸润巨噬细胞可以被区分为Ly6chi和Ly6clo两群细胞, 两者可同时存在, 但具有不同表达谱和功能. Ly6chi巨噬细胞可能在吞噬凋亡肝细胞后转化为Ly6clo巨噬细胞. F4/80lo CD11bhiLy6clo巨噬细胞表达典型的M2型基因, 如: Arg1, Mrc1, Fizz1 , 以及能中和IL-1α及IL-1β促炎作用的诱饵受体IL-1R2, 具有抗炎和组织保护作用; 而F4/80loCD11bhiLy6chi巨噬细胞表达典型的M1型基因, 如: iNOS, CD86, CIITA , 以及炎症因子、趋化因子和受体, 如: TNF-α, IL-12p40, IL-1β, CCL2, CXCL-10和CCR2等, 具有促炎和加重肝损伤的作用; Ly6chi和Ly6clo的比值增加可加重肝损伤[37,40].
3.3 肝炎病毒感染
全球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B virus, HBV)慢性感染者超过3.5亿, 慢性HBV感染可引起严重的肝脏病变, 可发展为肝纤维化, 甚至肝癌[51]. 受到细胞和动物模型限制, 肝脏巨噬细胞在肝炎病毒感染中作用的相关研究较少, 且多集中在HBV感染. 最初被HBV感染的肝细胞释放IFN-α/β募集抗原递呈细胞, 包括肝脏固有巨噬细胞. 肝脏固有巨噬细胞产生IL-18和CCL3等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 激活NK和NKT细胞, 参与对抗HBV的早期免疫. 肝脏固有巨噬细胞还参与提呈HBV特异抗原到CD4+和CD8+T细胞, 形成HBV特异性T细胞, 而后者是清除HBV的主要效应细胞. 肝脏固有巨噬细胞还可产生IL-12和TNF-α等细胞因子, 促进CD8+T细胞增殖并产生IFN-γ, IL-12还能诱导CD4+ T细胞向促炎型Th1分化[34]. 因此肝脏巨噬细胞在HBV感染相关的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 肝脏巨噬细胞也参与了HBV诱导免疫抑制. 2014年, Bility等[52]采用免疫缺陷小鼠建立了一种含有人肝细胞和免疫系统的人源化小鼠(A2/NSG/Fas-hu HSC/Hep mice), 其易发生慢性HBV感染, 可用于模拟人类对HBV感染发生的免疫反应以及肝脏的免疫损伤. 研究者观察到在HBV感染上述小鼠引起的肝脏病变中出现了大量M2型分化的巨噬细胞, 而慢性乙肝患者也可以见到类似M2型巨噬细胞在肝脏的聚集; M2型巨噬细胞的数量还与HBV急性感染肝功能衰竭患者出现更严重的肝细胞坏死有关; 进一步研究证实HBV可促进巨噬细胞向M2型分化. 2013年, Wang等在人单核细胞株THP-1体外培养实验中也有类似的发现[53]. HBsAg可抑制TLR2配体激活单核/巨噬细胞表达IL-12p40和IL-12等炎症因子, 但IL-1β, IL-6, IL-8, IL-10以及TNF-α的表达不受影响. 因此HBV促进巨噬细胞向M2型分化可能是HBV诱导免疫抑制、逃逸免疫监控并持续感染的重要机制[53].
本文中我们主要引用了基于小鼠动物模型的研究, 虽然人类单核巨噬细胞的表面标志不尽相同, 但也存在相对应的细胞表型[6], 如: CD14hiCD16-CCR2+/CX3CR1lo单核巨噬细胞对应小鼠的CD11b+Ly6ChiCCR2+CX3CR1-单核巨噬细胞; CD14dimCD16+CCR2-CX3CR1hi单核巨噬细胞对应小鼠的CD11b+Ly6CloCCR2-CX3CR1+单核巨噬细胞, 且具有类似的功能.
4 结论
肝脏巨噬细胞参与肝损伤的各个阶段, 在各类肝脏疾病的病理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基于目前的研究报道和前期的实验结果, 我们推测肝脏固有巨噬细胞本身就由来源卵黄囊和骨髓的两组细胞构成, 但这两组细胞在表型和功能上有什么差别? 肝损伤后, 大量外周血单核细胞浸润到肝血窦, 分化为巨噬细胞, 这一群巨噬细胞和肝脏固有巨噬细胞有什么异同? 不同原因引起的肝脏损伤微环境对巨噬细胞的分化有什么影响? 解析不同来源肝脏巨噬细胞在不同病因导致肝损伤过程中表型分化、生物学作用的动态变化及其分子机制, 对理解肝损伤的病理过程, 探索以肝脏巨噬细胞为靶点预防和治疗肝损伤以及肝纤维化的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评论
背景资料
免疫微环境在各种疾病病理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 肝脏巨噬细胞作为肝脏局部免疫的重要组成, 不可避免地成为肝脏疾病基础和临床研究的焦点.
研发前沿
解析肝脏巨噬细胞的来源、表型以及在不同病因所致肝损伤病理过程中的作用, 探索以肝脏巨噬细胞为靶点预防和治疗肝损伤以及肝纤维化的方案.
创新盘点
本文结合最新研究进展, 对巨噬细胞、肝脏巨噬细胞的来源、分化及其在药物性、酒精性、非酒精性以及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的常见肝脏损伤中的作用做简要回顾.
应用要点
解析不同来源肝脏巨噬细胞在不同病因导致肝损伤过程中表型分化、生物学作用的动态变化及其分子机制, 对理解肝损伤的病理过程, 探索以肝脏巨噬细胞为靶点预防和治疗肝损伤以及肝纤维化的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同行评议者
李瀚旻, 教授, 主任医师, 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苏松, 副教授, 四川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肝胆外科; 王劲, 主任医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放射科
同行评价
深入揭示巨噬细胞与肝损伤相关的分子机制, 对于推进炎症损伤的机制研究和抗炎保肝治疗的疗效提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临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