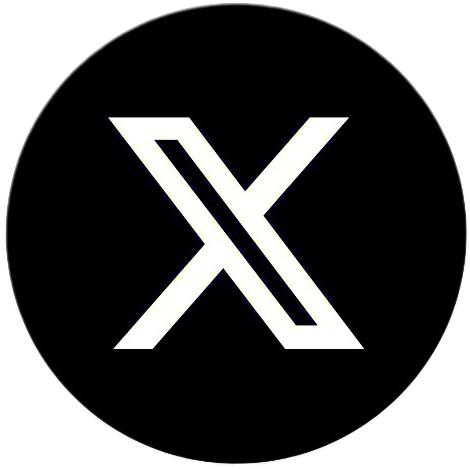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作为临床常见病与多发病, 目前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些年来, 随着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不断开展及PI-IBS概念的提出, 对于IBS相关病理机制的探讨已逐渐由功能性向器质性过渡. 为了将更加实用的药物应用于IBS的临床治疗, 研究者逐渐着眼于IBS与炎性因子失衡、肠黏膜屏障损伤的相关性研究. 探讨IBS细胞因子失衡与肠黏膜损伤的相关性, 是为了在探寻IBS有效治疗药物的征途中开发和评估新的治疗措施, 为更好的治疗本病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肠易激综合征; 细胞因子失衡; 肠黏膜屏障损伤
核心提示: 近些年来, 随着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不断开展, 对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相关病理机制的探讨已逐渐由功能性向器质性过渡. 为了将更加实用的药物应用于IBS的临床治疗, 研究者逐渐着眼于IBS与炎性因子失衡、肠黏膜屏障损伤的相关性研究. 探讨IBS细胞因子失衡与肠黏膜损伤的相关性, 是为了在探寻IBS有效治疗药物的征途中开发和评估新的治疗措施, 为更好的治疗本病提供新的思路.
引文著录: 陈婷, 唐旭东, 王凤云, 康楠, 王晓鸽. 肠易激综合征细胞因子失衡与肠黏膜屏障损伤的相关性.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5; 23(10): 1597-1602
Association between cytokine imbalance and intestinal barrier injury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Ting Chen, Xu-Dong Tang, Feng-Yun Wang, Nan Kang, Xiao-Ge Wang
Ting Chen, 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Xu-Dong Tang, Feng-Yun Wang, Nan Kang, Xiao-Ge Wang, Xiyuan Hospital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China
Supported by: National Key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No. 2013BAI02B0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s. 81373580 and 81173209;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s of Basic Research and Public Service Special Operations, No. ZZ070801.
Correspondence to: Xu-Dong Tang, Professor, Xiyuan Hospital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1 Xiyuan Playgroun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91, China. txdly@sina.com
Received: December 11, 2014
Revised: December 29, 2014
Accepted: January 9, 2015
Published online: April 8, 2015
0 引言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以腹痛或腹部不适为主要症状, 排便后可改善, 常伴有排便习惯改变, 缺乏可解释症状的形态学和生化学异常[1]. 本病为世界范围内的多发病,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一项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本病的全球发病率可达10%-30%[2-4]. 本病虽对患者的生存期无明显影响, 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5]. IBS发病机制复杂, 既往研究对本病的病理机制探究颇多, 多以遗传易感性、脑-肠轴调节异常、胃肠道动力异常、内脏感觉异常、精神心理异常、肠道菌群失调等为着眼点[6-10]. 现代医学多将IBS作为功能性肠病进行解读, 将消除患者顾虑、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作为其治疗目的. 自20世纪50年代起, 英国学者Stewart[11]提出了早期胃肠道感染与肠道炎症的相关性, 感染后肠易激综合征(post-infectiou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PI-IBS)或称炎症后肠易激综合征(post-inflammatory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PI-IBS)这一疾病继而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成为研究的热点. PI-IBS概念的提出及对其病理生理机制的探讨, 为探究IBS细胞因子失衡与肠黏膜屏障损伤的相关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1 IBS与细胞因子失衡状态的相关性研究
细胞因子是由免疫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NK细胞等)和某些非免疫细胞分泌的一类具有广泛生物学活性的小分子蛋白质, 对机体感染、免疫应答、炎症反应等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12]. 根据细胞因子在炎性反应中的作用, 可将其分为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两类. 促炎细胞因子主要由Th1细胞介导, 包括白介素-1(interleukin-1, IL-1)、IL-2、IL-6、IL-12、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TNF-α)、干扰素-γ(interferon-gamma, IFN-γ)等; 抗炎因子主要Th2细胞介导, 包括IL-4、IL-5、IL-10、IL-13等. 正常生理状况下, Th1亚群与Th2亚群通过分泌细胞因子进行相互调节, 维持比例平衡. 而病理状况下, 病变局部微环境改变, 促使该平衡稳态被打破, 表现为某群细胞占优势的免疫模式[13]. 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14], 尽管本病发病机制未明, 因促炎细胞因子与抗炎细胞因子失衡而造成的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俨然也是IBS重要的发病机制之一. Chen等[13]研究表明, IBS患者及PI-IBS患者血清及结肠黏膜组织中存在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失衡状态, 且IBS患者与PI-IBS患者血清及肠黏膜组织中细胞因子的失衡水平并不相同. 其研究发现, PI-IBS患者结肠黏膜IFN-γ mRNA及蛋白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及IBS-D患者, 但正常组与IBS-D患者并无明显差异; 而PI-IBS患者IL-10 mRNA及蛋白表达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及IBS-D患者, 正常组与IBS-D患者血清及肠黏膜组织中该细胞因子的表达亦无明显差异. Darkoh等[15]研究发现, IBS-D患者血清及粪便中TNF-α、IFN-γ、IL-1β的浓度明显高于健康志愿者, 而IL-10的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志愿者. Charles进一步发现, PI-IBS患者的细胞因子水平与IBS-D患者细胞因子的水平表达并无明显差异, 但PI-IBS与IBS-D两组患者与正常志愿者之间其细胞因子的表达并不相同. 提示两者虽发病原因不同, 但可能存在同样的免疫应答损伤机制. Ortiz-Lucas等[16]一项系统综述表明, 部分研究显示IBS-D患者血清中存在较高浓度的促炎因子(TNF-α、IL-1α、IL-6、IL-8)和较低浓度的抗炎因子(IL-10).
细胞因子作为免疫应答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与IBS的发病密切相关[17]. 随着对IBS与细胞因子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的失衡在IBS的发病机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目前对于细胞因子的作用途径及作用靶点尚未有统一定论, 因此对IBS发病机制的探析仍需进一步研究.
2 细胞因子在肠黏膜屏障损伤中的作用
肠黏膜屏障主要由机械屏障(肠上皮分泌的黏液、肠上皮细胞及其紧密连接等)、化学屏障(胃酸、胆汁酸、溶菌酶、各种消化酶等)、生物屏障(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和免疫屏障(肠道相关淋巴组织、吞噬细胞、sIgA、防御素等)组成[18]. 肠黏膜屏障的稳定性是胃肠道发挥其正常功能的重要保障, 且其结构的构建与功能的正常发挥又与肠道微生态及胃肠道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9]. 作为肠黏膜屏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机械屏障主要由肠上皮细胞及相邻细胞间的连接构成, 其连接方式包括紧密连接、黏附连接和缝隙连接, 而紧密连接在维持肠黏膜屏障的功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20,21]. 紧密连接主要由occludin、claudins、JAMs等跨膜蛋白组成, 他们再与连接复合物蛋白(ZO-1、ZO-2、ZO-3等)、细胞骨架结构(微管、微丝、中丝)共同构成紧密连接复合物. 跨膜蛋白通过连接复合物蛋白与细胞骨架连接在一起[22,23]. 肠道作为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的主要场所, 决定了肠黏膜屏障在维系人体与外环境的稳态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要选择性吸收水和营养物质、排泄代谢产物; 另一方面还要形成机体内部与外界环境的屏障, 既要与肠腔内的大量益生菌共存, 又要防止致病菌的侵袭与挑战[24-27]. 作为胃黏膜黏液层之后抵御微生物和抗原的第一道防线, 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是肠黏膜屏障结构与功能的基础.
肠黏膜屏障损伤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其中可涉及微生态、免疫及分子生物学等诸多领域[28]. 早期研究[28]结果表明, 肠黏膜屏障损伤多与黏膜酸中毒、氧自由基活化、细胞因子及炎性介质、中性粒细胞(neutrophile granulocyte, PMN)黏附及细胞凋亡有关. 而IBS所致的肠黏膜屏障损伤多与肠道低度炎症、细胞因子释放等密切相关[29].
细胞因子在肠黏膜损伤中的作用尚不十分清楚, 而促炎因子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早期研究[30-32]表明, 促炎细胞因子通过破坏细胞间紧密连接继而引起肠黏膜损伤. 不同种类的促炎细胞因子对肠黏膜紧密连接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 IL-1β主要通过降解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 NF-κB)抑制蛋白, 激活NF-κB, 抑制occludin转录启动子的活性, 从而导致其蛋白表达下调, 但细胞紧密连接的破坏是否因occludin蛋白的移位而引起, 有待进一步研究[33]; IL-6通过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信号传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途径激活NF-κB, 诱导细胞间黏附因子的表达, 促进炎症时中性粒细胞与上皮细胞的黏附作用[34]. TNF-α引起肠黏膜屏障功能损伤的部分机制已被阐明, 如TNF-α可降低紧密连接蛋白ZO-1和occludin的基因表达、改变紧密连接蛋白的分布、重组肌动蛋白骨架、抑制肠上皮细胞膜Na-K-ATP酶以激活NF-κB等[14]. 而在诸多细胞因子的相互作用中, TNF-α可能起到了主导作用.
TNF-α是一种具有广谱生理和病理效应的细胞因子, 主要由单核细胞核巨噬细胞分泌, 是肠黏膜屏障损伤的重要启动因子, 在细胞因子复杂的连锁反应中, 可能起到核心作用[35,36]. 该细胞因子一方面能通过激活NF-κB启动基因转录, 另一方面可诱导多种促炎细胞因子如IL-1β、IL-6、IL-8等的产生, 形成级联放大效应, 进一步加强对肠黏膜的损伤[24]. 多项研究表明, TNF-α引起细胞紧密连接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可能有多条信号通路参与其中, 主要有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yosin light-chain kinase, MLCK)途径、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 PKC)途径及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途径[14]. 而在其众多信号转导途径中, 对MLCK途径的研究较为全面. TNF-α通过MLCK途径引起肌球蛋白轻链的磷酸化以改变细胞骨架, 继而引起紧密连接蛋白结构的改变. TNF-α可通过PKC途径诱导细胞程序性凋亡, 故部分研究认为TNF-α引起肠黏膜通透性增加, 是由于细胞凋亡引起的[36]. 但在Marano等[37]的研究中, TNF-α引起Caco-2细胞通透性增加, 在细胞发生凋亡前就已经出现, 证实这种破坏作用并不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引起的.
3 IBS与肠黏膜屏障损伤
IBS发病机制未明, 既往研究多将IBS作为功能性肠病进行解读. 近十年来, 研究者将更多兴趣着眼于肠黏膜屏障损伤与IBS的相关探讨, 亦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肠黏膜通透性增加、低度免疫活化与IBS症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38]. 多项研究[38,39]表明, 部分IBS患者肠道存在低度免疫活化和肠黏膜屏障功能障碍, 这在PI-IBS患者中表现尤为明显. 由免疫细胞介导的炎症介质释放可能是肠黏膜屏障功能改变的源头, 肠道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同时可通过脑-肠轴触发内脏高敏感性, 进而引发IBS的一系列症状. 肠黏膜屏障损伤可能存在于任一分型IBS患者的肠道中, 尤其结肠与空肠部位, TJ蛋白的分布与表达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变[40,41]. 一项临床研究[40]结果表明, 与正常志愿者相比, IBS患者结肠组织中ZO-1和occludin蛋白水平明显降低, 但IBS-C、IBS-D、IBS-A患者之间紧密连接蛋白的分布与表达并无明显差异. Piche等[42]研究发现, IBS患者结肠组织的通透性明显高于健康者, 且活检组织中ZO-1 mRNA明显降低. 此外, 用IBS患者的结肠组织分离的上清液用于体外Caco-2细胞培养, 结果发现Caco-2细胞单层的通透性明显增加, 而细胞培养跨膜电阻明显降低, Real-time PCR结果显示Caco-2细胞的ZO-1 mRNA水平明显降低. Martínez等[43]研究发现, IBS患者结肠黏膜组织中肥大细胞数量增多且存在活化, claudin-2的表达增多, occludin蛋白磷酸化减少; 另一方面, IBS患者结肠黏膜中肌球蛋白激酶的表达明显增多, 肌球蛋白磷酸酶的数量减少, 从而增强了肌球蛋白的磷酸化. 以上分子结构的改变, 均可引起紧密连接超微结构的改变, 进而导致紧密连接打开, 从而导致肠黏膜屏障破坏, 肠黏膜通透性增加. Wilcz-Villega等[44]研究发现, IBS患者肥大细胞数目增多与肠黏膜通透性增加密切相关, 体外实验表明肥大细胞脱颗粒后释放的胰蛋白酶可显著增加肠黏膜上皮通透性, 降低紧密连接蛋白JAM-A及CLD-1的表达, 从而破坏肠黏膜的完整性. 由此可见, IBS患者肠黏膜屏障中紧密连接蛋白表达的减少及连接复合物蛋白位置的重塑均可显著影响肠黏膜的屏障功能.
4 中医药对于IBS炎性因子失衡、肠黏膜屏障损伤的作用研究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药治疗强调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 其多靶点的治疗优势对于IBS的重叠症状格外显著, 但其作用靶点与通路并不明确. 近些年来, 随着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进展, 大量体内实验与体外实验皆表明中药单体和复方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多原因所致的肠黏膜屏障损伤并可改善IBS炎性因子失衡状态,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医药防治IBS肠黏膜屏障损伤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胡俊等[45]研究表明, 中药灌肠液能通过降低活化的免疫细胞数目和上调抗炎因子及增强其抗炎活性, 纠正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失衡状态, 从而达到治疗IBS-D的目的. Cao等[46]研究发现, 中药单体黄连素可通过MLCK-MLC磷酸化信号通路拮抗促炎因子TNF-α与IFN-γ对肠上皮紧密连接结构和功能的破坏, 从而对IBS患者的肠黏膜屏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Liu等[47]同样发现, 藿香正气液能明显改善PI-IBS大鼠肠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 调控ZO-1和occludin蛋白的表达与分布, 从而增强肠黏膜屏障功能, 改善炎症所致的肠黏膜通透性增加. 一项临床研究[48]结果表明, 四君子汤可增强巨结肠儿童肠黏膜屏障功能, 该方既可增强肠道免疫, 又可维持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 由此可见, 采用中药单体或中药复方对肠黏膜损伤进行干预, 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因此, 进一步探寻有效中药对于IBS肠黏膜屏障损伤的调控机制, 则可为中药调控IBS肠黏膜损伤的靶向治疗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5 结论
研究IBS细胞因子失衡与肠黏膜屏障损伤的相关性, 是为了在探寻IBS有效治疗药物的征途中开发和评估新的治疗措施, 为更好的治疗本病提供新的思路. 现阶段对于IBS的药物治疗, 多采用解痉药、肠道动力感觉调节药、止泻剂、微生态制剂、抗抑郁药等[49,50], 以上药物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IBS的单一症状, 但其临床疗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IBS肠黏膜屏障损伤这一病理机制的提出, 可为探索治疗IBS的药物提供新的靶标. 目前, 新型生物制剂英夫利昔单抗是一种抗TNF-α人鼠嵌合体单克隆抗体, 可通过拮抗免疫炎症发病通路中起关键作用的促炎因子TNF-α而起治疗作用[51], 该药已逐渐应用于炎症性肠病的治疗, 但其价格昂贵, 俨然不能作为治疗IBS的首选药物. 因此, 探寻有效中药及其作用机制便为IBS的治疗开启新的篇章, 亦为中药治疗本病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评论
背景资料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为世界范围内的多发病,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虽对患者的生存期无明显影响, 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既往研究多从遗传易感性、脑-肠轴调节异常、胃肠道动力异常、内脏感觉异常、精神心理异常、肠道菌群失调探究本病.
同行评议者
王小众, 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消化内科
研发前沿
中医药多靶点的治疗模式对于本病优势明显, 大量体内实验与体外实验皆表明中药单体和复方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多原因所致的肠黏膜屏障损伤, 但其作用靶点与通路并不明确.
相关报道
Charles等研究发现, IBS-D患者血清及粪便中TNF-α等促炎因子的浓度明显高于健康志愿者, 而IL-10的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志愿者. PI-IBS患者的细胞因子水平与IBS-D患者细胞因子的水平表达并无明显差异, 提示两者虽发病原因不同, 但可能存在同样的免疫应答损伤机制.
创新盘点
本文对IBS细胞因子失衡与肠黏膜屏障损伤的相关性进行综述, 为IBS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应用要点
研究IBS细胞因子失衡与肠黏膜屏障损伤的相关性, 是为了在探寻IBS有效治疗药物的征途中开发和评估新的治疗措施, 为更好的治疗本病提供新的思路.
名词解释
感染后IBS(PI-IBS): 急性肠道感染恢复后出现符合IBS罗马诊断标准的临床症状, 而此前无IBS相关表现. 其诊断主要基于症状, 具有回顾性特征.
同行评价
本文对IBS细胞因子失衡与肠黏膜屏障损伤的相关性进行综述, 为IBS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